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b�ػ���еďı������о�
ժҪ�������b�ػ���Џı��F(xi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W����(j��)�ж���һ��혏ġ���Ϣ�����Ӱ푡����ܴ�Ӱ푵ďı������팦������?zh��n)���Ϣȱ���J֪�����H�ڹ��_����협�(y��ng)���˵��b����Ҋ����˽��Ҳ���\�Ӽ{������혏ġ�Ҏ(g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Ӱ푡������ı��ߌ�������?zh��n)���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Д࣬�����˵õ����˵ĽӼ{�������협�(y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顱�����_혏ĈF�w���(qu��n)�����b����Ҋ������(n��i)�IJ���혏����ɷN��Ӱ푡����ܡ��ı�Ӱ�Դ��Ⱥ�w�Ŀ��ƣ����ݵ�λ���b�p����Ⱥ�w��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Ե������nj����˂��ı���׃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c��ͬ�r�����ı�Ӱ�Դ��֮�g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Ԓ�Z��(qu��n)����(j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ض����и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ı���Conformity������ָ���w���Լ��đB(t��i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О��cȺ�wҎ(gu��)����ƥ����О���1���҂���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ı����ƺ���һ���H�x�~���ǂ��wȱ����Ҋ�ı��F(xi��n)���c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ơ�������Ӱ�����S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ȳ��Z�������Ƶ��~�x���҂����T�яı��߷Q�顰���^�ݡ���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W�҅s������ͬ�Ľ�����J��ʹ����(sh��)����ďı��О�һ������ďı��О�ֻ���^���M�����x�τ���ı�Ч��(y��ng)�����m(x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Ҳ�����f���˂������ٶ���һ���ď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^�ı��О������s�����Լ��ı��ij̶Ⱥ͏�(f��)�s����
�ڂ��y(t��ng)�����b������У��ı��ߵı����H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sh��)�ղؽ�ġ������ߡ������˽�v�������ĕr���L��ͮ��ҵĂ����L��ȱ���b�ؕ�������Ļ������B(y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ű��˻��ۡ���Ԓ�Z�����ڲ�֪��Ȼ�ď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^��Ҳ�в��ق��w��]�N�N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顱���`���Լ����挍��Ը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ı��˻�?q��)��ҵę?qu��n)��֮Ӌ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b���е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顱���Y(ji��)����c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F�������L�����o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t�����h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ݱ���
�@Щ������ؾ��Ɍ����b��Ⱥ�w�x��(qu��n)�ˏ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^������ֻ�Ǟ��҂��ʬF(xi��n)�ˡ���(qu��n)�ˏ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δ���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әC����ˣ������y(t��ng)�����b�ػ���е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W��ҕ��֮���M�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҂����^�J֪�ı��F(xi��n)�����b�ػ�ӵ�Ӱ푡�
һ�������b�ػ���еďı��F(xi��n)�����
�ı��F(xi��n)���ڕ����b���I(l��ng)����^ͻ����ԭ��Ҳ�^���(f��)�s�������¿ɷ֞顰��Ϣ�����Ӱ푡���Informational social influence���͡�Ҏ(g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Ӱ푡���Normative social influence���ɷN����ǰ��Ӱ푵ďı�Ⱥ�w���ڌ��Լ����J֪���Д�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˱�����Ϣʧ�`�����T�ѱ��˵ķ���(y��ng)���(qu��n)�����Д������Լ��ą����c���ı��߲��H�����@�О���협�(y��ng)�ڏı�Ӱ�Դ���ڃ�(n��i)��Ҳ�Jͬ�����^��Ҳ��һ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֪�Լ����Д������_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ӭ�ϴ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f��)���ڱ����Ϸ��ı��˵��^�c������(n��i)�ĈԳּ�Ҋ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W�Ҍ���ı�ԭ��Q�顰Ҏ(g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Ӱ푡���Normative social influence����
���ˏ����ڡ���ҫ����ӛ�d��һ�l��Ϣ���Ǖ����b���I(l��ng)���б��^���͵ďı��F(xi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g��ͬȺ�w�ı������ԭ����С���Ϣ�����Ӱ푡���Ҳ�С�Ҏ(g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Ӱ푡���
����º�������r����ij�������յ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ɽˮ֮���ij�ҹ��˽�ȥģһ�������c��º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ʾ���e��ij��ż������һҊ��ЦԻ�����÷�ij�����I������º���@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֪֮����ij��Ի�����汾��ij�����أ���(sh��)��ǰij�҇L��ȥ������ģһ���ԫI������º���@����Ի������֪���Խ��һ�^������ij��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ȡ����º����ҕ�ɱ���֮��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ij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e�����c��Ի����ij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ij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І�֮�ߣ�ij�ׇ@Ի����ij������Փ���r����֪�����º�������Ԓ���Ž�֮ͬ������ӠҲ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ij���ˡ��ďı��T��?q��)��ڵ��͵ġ��?g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Ӱ푡���ԭ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Ǚ�(qu��n)���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DZ��e�͙�(qu��n)���ġ���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ݵĵ����ڴ˾����£�ij���˼�Ҫ�挦�c�Լ���Ҋ����ı��e��߀�����(qu��n)���Ĵ��ڣ���˾����^��ďı����퉺������Ⱥ�wҎ(gu��)ģ��һ���ԁ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ij�����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ڈ����e���b����Ҋ�������ڡ�����º�������ď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Ⱥ�wҎ(gu��)ģ��ռ��(j��)��(y��u)������Ⱥ�wҎ(gu��)ģ�ǡ�Ҏ(g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Ӱ푡�����ҪԪ����Ⱥ�wҎ(gu��)ģԽ�����˂�Խ���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w�挦Ⱥ�w��һ�����J֪�Y(ji��)���r������ܵ����퉺�������֪����ʹ�����ò������ı����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f���S������Խ��Խ���R�������c�����(sh��)����Ҋ�������Ķ��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˸��п��ܷ���Ⱥ�w�ěQ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ij���ˡ������º����ĵ�λҲ�����ı���ԭ��֮һ����邀�w��Ⱥ�w�е������λԽ������(qu��n)��Խ������Խ�����ı�����֮��Ȼ���ď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ҕ�ٞ�����О��䌍���ھS�o�Լ����b�p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J�������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o���ڳ��J�����b�p���ĵ��£����Dz�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ˡ��IJ������ڙ�(qu��n)���ļӳ��£��ď����IJ��Ե��Գɹ���ʩ�����ڱ��e�ĸ������γ�Ⱥ�w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J֪��һ���ԣ��@�N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Ҳ��Ӱ�ij���ˏı���ԭ��֮һ��
���˙�(qu��n)�����ڈ������e���@ʾ���ďı������䌍Ҳ�c������?zh��n)���Ϣ�ē�˷���x���P(gu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J֪�����ģ���Ժ��΄�(w��)�ď�(f��)�s���ڏ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ǘO����Ҫ��׃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W�ҿ������ı�����邀�w�������ˌ�һ��ģ���龰�Ľ�ጱ��Լ��Ľ�ጸ����_�����ҿ��Ԏ����҂��x��һ���m��?sh��)��О鷽ʽ����Դ������W���x���MuzaferSherif���ġ��T���e�X����
�ڴˌ��������ԇ����Ҫ��һ���ڰ��ĭh(hu��n)�����Д�һ�����c���Ƅ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H�Ϲ��c���oֹ�ģ��l(f��)���ƄӬF(xi��n)����ij�N�e�X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M�ܛ]�Ќ�������ṩ�e�`�Ĵ��M���T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_ʼ�r��ԇ��֮�g����J֪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˺�������ԇ��֮�g���a(ch��n)���J֪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Д�����uڅ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ԭ������ڱ�ԇ�߶��o���_���Լ��Д�Ĝʴ_�������ԃA���ڲɼ{���˵���ϢԴ����K�γ��˱��^������Д����@�f�������w�o���_�����_�Ĵ𰸺����_���Єӕr�������ܵ������Д��Ӱ푡����wԽ�Dz��_�����͕�Խ��ه�e�ˡ�ǰ���c�ď���ͬ���b�p�ı��e���ڟo���_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?zh��n)�֮�e�����x���(qu��n)����ʿ���Д���S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o����һ�N���^���U�IJ��ԣ�����ı�ԭ��͌��ڡ���Ϣ�����Ӱ푡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Ҏ(g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Ӱ푡��c����Ϣ�����Ӱ푡����IJ�ͬ������ǰ�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˂����_��혏�����˽�²����Ӽ{����Ҳ�����f����Ҏ(gu��)����ԭ�����l(f��)�ď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Ǟ��ˑ�(y��ng)�����w��ģ���龳�½�Q���}�Ľ��]�������ڹ������ϸ��ʹ���Ҋ������(n��i)�IJ������ܡ�ij���˾͌ٴ����Ⱥ�����mȻ������Ĭ�J���ď����ͱ��e���^�c������δ���ĵ������Ӽ{�@һ�e�`�J֪����ʹ���ı���ԭ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ڡ�Ҏ(g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Ӱ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Գּ�Ҋ����(j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y�����ҕ�鮐�ƫ�x�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f��߀������e���Z�Թ�������ҕ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K�п����ڸ��N�����ܵ��ŔD������\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ԣ�
���˱���ɞ����˵ġ�����ᔡ�����Ҷ��ಽ��څ������̤�eһ���ͳ�����ֻ����ָ���ġ����^�B�����M���ɞ��ҹ����Č�����
�ڕ����b���I(l��ng)�����ı�������Ȼ���L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Įa(ch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Ǚ�(qu��n)�����ҵďı��О飬��Σ�����Ȟ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ָ����
�b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y��ng)�ǡ��F��o˽�������ɏķN�N�Ƕȡ����ơ������O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С���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ͬ����Ȼ�ƌW�����ܵ��S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ʹ�Y(ji��)Փ�����_������ƽ����ó�һЩ�����ġ��ĽY(ji��)Փ��
�b����֮���Ըе������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ďı��О���ѭ�ˡ�Ҏ(g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Ӱ푡�������(n��i)�IJ����J���Լ����x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l(f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ì������ơ����ġ����b���Y(ji��)Փ�Թ���֮���眫����ӛ��
�θ���ÿ���L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b���}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r������ӭ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LҊ����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Hδ�������}�R���棬�b�߲��ɲ�֪Ҳ��
�����ʡ�ӭ�����⡱�О鱳��ġ�Ҏ(g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Ӱ푡��䌍���dž������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b���硰�ı�Ӱ�Դ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cή�s
�����b��ʷ������Ҏ(g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Ӱ푡��͡���Ϣ�����Ӱ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Ǐ�(f��)�s������׃�����c�������Ӱ푵����w��(qu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P(gu��n)��Ҳ�cý��ę�(qu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P(gu��n)��߀�c�b��������?zh��n)���Ϣ��ģ�������P(gu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b�����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r�ڣ������r����֧���b�����C��(j��)��M��ģ���ԺͲ��_�������S����Ʒ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I���s���o����Ч���۷e�b������֪֮�R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ü�����ƫ�����y�γɹ��R�������ݳɟo��(qu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ه�āy�֡�������ͬһ����Ʒ����ͬ�b���ҵij�ʼ�J֪��Ȼ���M��ͬ���˕r����Ҫ�ԡ���s��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ʽ�_��ij�N���R�����˼���Ʒ�{�뵽�����Į�ʷ����֮����
�Ԃ������ή����R�h��(chu��ng)���ġ�̤��D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D1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ͱ�ղ���Pҕ�����E��20���o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l(f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Ҫ�Ĉ�ý����50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J�����R�h���E������ۻ�ُ�����H��20���o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ղؼ�֮һ��Ҳ�����Ї�������ĵ�һ���b����ң����b���Y(ji��)Փ�O�ߙ�(qu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ͬ�rҲ�춨�ˡ�Ҏ(g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Ӱ푡��͡���Ϣ�����Ӱ푡��Ļ��A(c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80��������x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_�����ʐ𡢄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x�����Ȟ�����ġ������b��С�M��Ҳ���m(x��)�ˡ�̤��D�����b���Y(ji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侎�롶�Ї��Ŵ�����Ŀ䛡�֮�����@һ���R���_�ɿ������⡰��Ϣ�����Ӱ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ͬ�rҲ��ζ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b��С�M���ɞ��b����ġ��ı�Ӱ�Դ����

�D1 �� �R�h��̤��D�� �����O(sh��)ɫ �v193.5�������M111.0���� �����ʌm����Ժ��
���ı�Ӱ�Դ��һ�����ɣ����h����Ҫ�|(zh��)�����Ʒ���̤��D�����b���Y(ji��)Փ���䌍���y���l(f��)�W�g(sh��)���Q���箔���b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̤��D���M���^ȫ���|(z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Z����?zh��n)ε��b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:ā�ĹPī���Ⱥ��L������@Ȼ�����f������Ȼ�������ڡ�Ӱ푡��a(ch��n)���đT�Ժ��˔�(sh��)����ďı��ߣ����g(sh��)ʷ�о��ߺ͕����b�ؼ�ҕ��̤��D�����R�h���E�ďı��О鲢δ���xȺ�ߡ����о��Y(ji��)Փ����׃��
Ȼ�����S�������Ї����g(sh��)ʷ�о�����u���룬�P(gu��n)���R�h��̤��D������?zh��n)��Д��ڇ���Ҳ������һ�N�Y(ji��)Փ����ͬ�ڇ���(n��i)�b����(qu��n)�����Д࣬����W���ձ��J�顶̤��D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R�h���E�����ľ���J��ˈD�ǡ�������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Mһ����Ʒ�ϼ��˿�ĵ��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䶨������ģ�����߾Ӻ��J��ˈD�dz���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䌣����Ҳ�����О�ġ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W��֮���Ա��F(xi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ı����О���ԭ�����ڣ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c�������b��С�M���ɆT�����ڎ�ͽ�����塢����ȷ�����H�����P(gu��n)ϵ��Ҳ����ͬһ�W�g(sh��)�F�w����Ҏ(g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Ӱ푡��o���o��������κΏ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S������W�ߌ��Ї��Ŵ��L���о���ȵ�������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ڡ���Ϣ�����Ӱ푡����߾Ӻ�ָ����
�@Щ�ˣ���ʮ���o�Ї��b����ďı�Ӱ�Դ����(j��ng)�����@�ӷ�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ڼ������Ʒ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Ŀ��Ŷȡ��@�����Ǻ��г�Ч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50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ղؼҺͲ����^�^�L߀�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Ї�֪���b�������Ļ��ϵę�(qu��n)����
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20���o����~�������Ї����о��ߵ�Ⱥ�wҎ(gu��)ģ��һ����Ҳ��u��������ij�N�̶����ѽ�(j��ng)�γ��µġ��ı�Ӱ�Դ�����Ķ����l(f��)�ˇ���(n��i)�b��Ⱥ�w�ďı����]��
�Ԯ����ղؼ���B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Ͷ���(sh��)�ؼ����ƣ��ǡ������b��С�M�����Ҍ��ı�����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֪2014�ꡰ�ή����H�W�g(sh��)���h���е�ʮ��λ���v���e�H�Ѓ�λ��ꑌW�ߕr�����ɰl(f��)���Ї@�����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]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ָ�������b��С�M���ɆT���Έ�������Ԓ�Z��(qu��n)�䵽���⣬���Ǜ]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B�����ԡ�Ԓ�Z��(qu��n)���䌍���Ǐı��ġ�Ӱ�Դ������ijһȺ�w��Ԓ�Z���ձ鹫�J����ζ���µġ��ı�Ӱ�Դ���γ������ġ����ġ��ͽ��]���ǿ�Ѩ���L���S���W�g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څ���S�������b���ķ����_ʼ�l(f��)���D(zhu��n)׃�����⽛(j��ng)����Ї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о��ɞ����g(sh��)�W���I(y��)�WλՓ�ĵĘ˗U���L��������D��W����̖�W������W�ȷ���Փ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b���ڬF(xi��n)�����g(sh��)ʷ�W�Ƽ�����Փ�Ď����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x�ϳɞ顰���˶��܌W�����ķ�������Щ���x��ˇ�g(sh��)ԺУ�ČW����Ҳ�������Г�(j��)���|(zh��)�ə�(qu��n)�����ҵĽY(ji��)Փ���S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m(x��)�l(f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y(t��ng)�b����(qu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ă�(y��u)�ݱ���uϡጣ����g(sh��)ʷ�о���Ҳ������ä���b����ġ����ۡ����_ʼ����ҕ������(qu��n)���b���ҵĽY(ji��)Փ��
�����о��ߏı��Ļ��A(c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ijλ�����ۡ��Ĕඨ���λ������ȶ�ĽY(ji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ڴ��b����(qu��n)���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ŷ������C��(j��)����ʹ�@Щ�C��(j��)ֻ�ǽ������ԈA���f��߉�����Է�������ɽ�D�����D2�����b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M����δ���ó��F�C�C���ˮ��鱱�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E���f�������F��Ʒ�������会ā����ʽ���ȡ��D�Ļ��C�ı�����ʽ�Լ�������߉�P(gu��n)ϵ��ʹ�����g(sh��)ʷ�W�猦���b���Y(ji��)Փ���ձ��J�ɵđB(t��i)����

�D2 �� ����(��)����ɽ�D�� �����O(sh��)ɫ �v44.1�������M116.8���� �������^��
�ڴ����x�������g(sh��)ʷ�о��ďV���c����ƺ��ѽ�(j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b���W���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֮�g�����ǻ��a��ƽ�е��P(gu��n)ϵ��20���o����ʮ������b�������Ժ����J�����g(sh��)ʷ�о��Ļ��A(ch��)���b���W����Ҳ�Ĵ_������˕r���b��Ⱥ�w�������g(sh��)ʷ�W���b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|(zh��)�ɺ͔��·����ij��SҲ�@ʾ���b��Ⱥ�w�ă�(y��u)Խ�к͙�(qu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b��Ⱥ�w���H�������b��������?zh��n)εĽ�ɫ��ͬ�rҲԇ�D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Ʒ����ǡ��?sh��)����g(sh��)ʷ���Ю��У��ЌW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Ї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ڵ��Ї��L��ʷ�о����x�顰�b���WҕҰ�µ��L��ʷ����
Ȼ�����r�^���w���F(xi��n)�����g(sh��)ʷ�W���ڸ���ԺУ�еİl(f��)չ����S�������b���W����20���o����ʮ����l(f��)���ԁ����s��N�Nԭ��ͣ����ǰ���b���Ҳ��ò����J�����Ї������b���W���J����δ���ܞ�V���x�������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g(sh��)ʷ�W�Ƶİl(f��)չ������֮�b���W��Ⱥ�wҎ(gu��)ģ��Ⱥ�w��������Ⱥ�w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ʬF(xi��n)��ή�s֮����
20���o50������b���җ��ʐ����u���g(sh��)ʷ�W�����d�������Mһ�����ϵ�ƪ�����鮋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^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ͬ�r�ַ������d���öػͱڮ��е�ɽˮ����顶�δ��D������ķ������J��ڮ��;��S��֮�gȱ���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ڽ��գ�ˇ�g(sh��)����W��ˇ�g(sh��)���ŌW�ѳɞ����g(sh��)ʷ�W���M�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Ҫ����֮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W�g(sh��)���y(t��ng)���Ї����g(sh��)ʷ�о����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Փ����ҕ�njӳ����F��һ�����ɂΡ������桱�ĕ�����Ʒ���·�������ҕ�ǵ�Փ�C֮�����ܡ������ŷ��ء�ʹ�x�߽������P(gu��n)�о��ɹ������^�b���W�I(l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f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ӡ80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С�M�����о��ɹ������r�о�����ҪӰ����ijɹ����F(xi��n)����Ȼ������Ҳ����ĬĬ���ŵĕ����b���W�ߣ������80����Ї������b�����x�����@Щ�W�ߵĂ���ʽ�о��ں�F(xi��n)���W�g(sh��)ҕҰ�о��@�������o������ʹ�Ђ��e���ʵ��b������ż�гʬF(xi��n)��Ҳ�o�����鷽��Փ�ڌW�ƌ����M���ƏV�����w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b���W���о��ɹ��ȡ�ȱ����Ⱥ߶ȡ���Ҳ��ȱ���V���c���ȡ����@Ҳ�������b���I(l��ng)��ı�Ӱ�Դ��ή�s������(y��ng)�أ��˂�����(j��)�@һӰ�Դ���ı��Ď��ʾ͕�������
һ��Ӱ�Դ�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ጷŵ���Ϣ�ڏı�Ч��(y��ng)���Ƅ��±�Ȼ���ɞ顰�ձ���ܡ�������ʯ���t��Մ�����紺�D�����D3���r�J�飺
����ֻҪ�ؑ�����1027��Ĺ������紺�D���ڶ�ʮ���o��ʮ����r�ж����|(zh��)��֮��Ȼ���Մt�ў�W���ձ���ܞ�ʮһ���oɽˮ���Ļ���֮�����Ϳɸ��X�@�������Á����ijɾ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Ʒ�܉�ɞ��ձ��J�ɵ����E���_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Ҫע�������ʯ���t���ԡ��ձ���ܡ���ָ���W�g(sh��)��ę�(qu��n)���W�������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W�Ҍ��@ЩȺ�w�����ɵġ��ı�Ӱ�Դ���Q�顰�ٔ�(sh��)��Ӱ푡���minority influence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ٔ�(sh��)��Ӱ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qu��n)���Լ�Ⱥ�wҎ(gu��)ģ�R����һ��r�������紺�D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E���@һ�Д�ͳɞ��������J�������˂��ı�����ϢԴ��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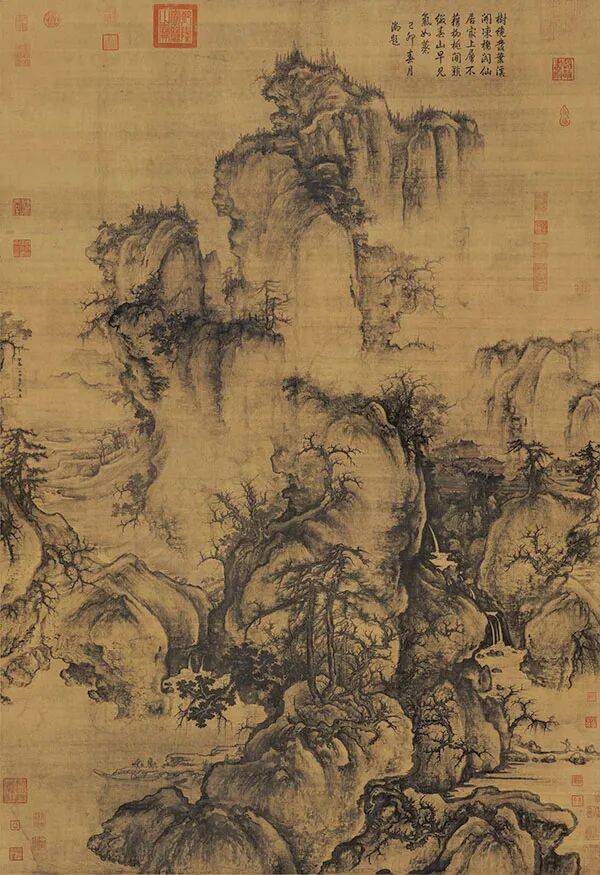
�D3 �� �������紺�D�� �����O(sh��)ɫ �v158.3���ף��M108.1���� �_�����ʌm����Ժ����
��һЩ�O�˰�������Ӱ�Դ��Ⱥ�wҎ(gu��)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H�܉�Q����Ʒ����?zh��n)Ό��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ķ���Ч�������?0���o90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n��i)ij���u���ij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ǧ�ġ���ʯϪɽˮ�D�����ۃr�����f�����º�����_���x������λ̩�������b�ؼ҅s���ˮ��o����һ��һ����ȫ�෴���b����Ҋ���I�Ҟ����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u��˾���Ϸ�ͥ����ͥί�Ї�������ֽM��ʮλ�b���Ҍ��ˮ������b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J��ˮ��ǂ�������ԺҲ���˽Y(ji��)Փ�ж����u��˾���V�����@���b���L�������҂����y����Ӱ�ԴȺ�wҎ(gu��)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_���x����ͬ���ղؽ�ı���Ӱ�Դ����Ӱ����ஔ�������S����V�A�У�ʮλ�b�،��ҵ��b����Ҋ֮�����܉�l(f��)�]����Ч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ṩ�˽^�����x�ϵĿƌW����(j��)���@Ȼ����Ⱥ�wҎ(gu��)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ռ��(j��)�˃�(y��u)�ݡ�
�����ı�Ӱ�Դ֮�g�ĸ�������әC
����_��ʮλ�b���ұM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L���б��F(xi��n)����Ӱ�Դ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_���x�����䌍��ͬ��20���o80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b��С�M���ijɆT������ͬһӰ�Դ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Ҋ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Տı�Ӱ���Փ���҂�����ҕ����Ӱ�Դ��(n��i)����һ���Գ��F(xi��n)�ˆ��}����Ⱥ�wһ���Եı�������Ȼ���ı��ʵ��@���½������ı�Ӱ�Դ֮�g���F(xi��n)��һ�r���˂�����Ӱ�ԴȺ�w�����ζȾ͕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һ����ʹ�������͌�Ⱥ�w��Ҋ�������ɵĂ��w�ҵ���֧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ṩ�˿��ԑ��ɵĿ��g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˂�������(sh��)��Ҋ�����Д����յ���ه�ԣ����ı����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ʯϪɽˮ�D�������L���ij��F(xi��n)���ǵ��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xȺ��ͨ�^�˽��@һ�¼������F(xi��n)����Ӱ�Դ�IJ��M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b�����^�̲���һ���ڿƌW���x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C���C�ٵ��^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b����(qu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ƴ���^�̣����l�ę�(qu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l��Ԓ�f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l�������c��λ���^Ӳ��
�ɴ˿�Ҋ���ı�Ӱ�Դ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Բ�����(w��n)�����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W�g(sh��)�F�w����ͽ�P(gu��n)ϵ�����ص�Ӱ����֮�g��������Ԓ�Z��(qu��n)�����ض����и����C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b�ؽ��Ӱ�Դ�༯���ڌm͢����Ҫ���Ե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䌏���b���^��̫�A���ڡ���(n��i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ā��Ʒ�|(zh��)����ƫ�Ì���Ž��ʶ�������|(z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m͢�ٻ¼��F���A�ӵČ����b���^�ɾ������ɼ�Ժ�w���ҵ��x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ʢ֮�r��Ժ�w���ҹ�Ԃ�������ٽ����䮋�ߡ������M���ǂ����μo��������߅���ѡ����όW�������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_��Ժ�w���һ�?q��)m͢���ҵ���Ʒ��ÿһ�S�r������ʮ��𡱣���Ԫ�ļ������ܵ���Ʒ�����ܝM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Ȼ�����S�����T�b�ؼ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ĵļ���ʽ����ͽʽ�b��Ⱥ�w�ɞ����µ�Ӱ�Դ���ı�Ⱥ�w�S֮���F(xi��n)�����K���Ԟ����ߣ��t�ķ��S����֮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t�S����֮�������S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ȥ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d���ɽ��ͻ��ݵȵصĕ����b��Ⱥ�w�S�S��ԇ��ԇ�D����(zh��n)��ȡ��Ӱ����صą��T�ı�Ӱ�Դ������ֱ�ӵķ�ʽ���Ƿ�����ҕ�������I�S���T�b�p�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ݵ�ղ���Pֱ�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ӵ��b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J�顰���ϸ����m�Õ�����ȻҊ���}����ī�E�����I��և�������l(f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ߵ��Q���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۷����°���Ү���Ĵ�đ��Փ�������d���Ԫ��t���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T�ڶ���Ӱ�Դ�����S�̣������϶����tϹ?ji��)h����϶�����ҕ�ߠ�����
�Dž��T�b��Ⱥ�w���څ��T�b���Ҳ��z�����Ĺ����О������ڌ��Լ����ܞ��µďı�Ӱ�Դ���ЌW���J���䱾�|(zh��)�ǽ�(j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֮�������^���ڹP�߿�������(j��ng)�����ػ��Sֻ�����еĴ�ҪĿ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˹���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Փ�����ᆖ��
���˖|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ҹ�ل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ʲô����؝����Ұ������ؔ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qu��n)�Z�������λ�������@Щ�ĽK�OĿ����ʲô�أ��y��ֻ�Ǟ��ṩ�˂����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ጵ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ͬ��z��֮�������ĝM����֮�������J�ɳ��J֮�B(t��i)�ȼ���Մ?w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ע�����@�����҂�������Ŀ�˫@�õĺ�̎�����҂����dȤ�ļȲ��ǰ��ݣ�Ҳ���ǿ옷������̓�s����
�²��D�ڡ����ݵĽ��]����Ҳ������Ƶ��^�c��
���@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Ė|��Ҳ���H�H������ؔ���ϡ�һЩ�dz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ؾ۔�ؔ�����M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˓]��֮�á�����҂��Գ������Ե�ؔ��(w��)ҕ�c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Ҳ�S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Ŀ��е��y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҂������ڷe��ؔ����ͬ�r�������䌍Ҳ���Aȡ���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҂��Ͳ�������ˡ�
������˹�ܺ͵²��D�Ľ�ጌ��H�ό���(y��ng)���Ї������Եġ����ӡ������Ӽ��P(gu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ͬ�rҲ�c���u�ܲ��ɷ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˵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ҏ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ܵ��ı����ص�������ͬ�rҲ�nj����҃rֵ���F(xi��n)���J�ɡ����ӡ����H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P(gu��n)ϵ�еĵ�λ�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漰�����e�˽��ܵĿ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Լ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qu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ڕ����b���^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qu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ڵش_�J�������Ҍ����з��x�����Ա��o�Ϳ�ҫ�@һ����ʹ֮�Ȳ��ܓp������ϲ�ۡ����ɞ��b��Ⱥ�w�еďı�Ӱ�Դ����ζ�������܉�Ŕ�Ԓ�Z��(qu��n)���ɞ���Ʒ��?zh��n)ε��ڙ?qu��n)�ߺͽK�O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Ԓ�Z��ͬ����һ�㣬�ڛQ����Ʒ��?zh��n)Ό��Ե�ͬ�rҲ�Q������rֵ�������ı��ߌ���څ֮���F��С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Լ��ղص���Ʒ���С����̡����߸����ϵę�(qu��n)���к�һ�Z��Ǭ���ę�(qu��n)���У��Լ��r�����ܵ��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J��ĸ��X�����b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b���^���г��F(xi��n)ʧ�`������ͨ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ʡ����뷽�O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M�С�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ӵ���Ҫ�Ժʹ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ġ��Y(ji��)�Z
�ڕ����b�ؽ����˂��ı���ԭ���H���(f��)�s���еďı������ܡ�Ҏ(g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Ӱ푡����ı�������?y��u)��˱��ֺͱ��˵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ʹ�Լ��ɞ��xȺ�߶���ȡ���ُı�����(qu��n)�ˏı������mȻ�����@�О����Jͬ���˵��b���Y(ji��)Փ�����ڃ�(n��i)�ąs�Գּ�Ҋ���еĄt����Ϣ�����Ӱ푡����ı������b���ߟo���{���Լ���֪�R�M���ж����ڴ˾���֮��ֻ�����Ŷ���(sh��)�˻�ı�Ӱ�Դ���b���Y(ji��)Փ��
���y(t��ng)�����b�ػ���\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(f��)�s������P(gu��n)ϵ�W(w��ng)�j(lu��)֮�У����@���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F�w����ͽ�Լ����x����(qu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X�����u��(g��u)�ɵľW(w��ng)�j(lu��)�У�̎�����ĵ��Ǟ锵(sh��)����ďı�Ӱ�Դ��Ӱ�Դ���b�p����Ⱥ�w��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ݵ�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nj����˂��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Ӱ�Դ֮�g��������Ԓ�Z��(qu��n)����(j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ض����и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Ҫȡ���ı�Ӱ�Դ����ֱ�ӵķ�ʽ�����M�й��_�ķ��ı��О�����Ӱ�Դ���b���Y(ji��)�����H�����b�p���ȡ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ɞ�ı�Ӱ�Դ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С�ľS�o�������b��ʧ�`����ُ������Ҫô�ԡ�����ʾ�ˡ��ķ�ʽ�[���Լ���ʧ�`��Ҫô�Գּ�Ҋ���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ˡ��IJ��ԾS�o�Լ����b�p����







�l(f��)���uՓ �uՓ (0 ���uՓ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