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21������҂���Ȼ�x�������X��ľGɫ����
1904��7��15����44�q�Ķ��(g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X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㙉������Ȼ�o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X��Ѹ�����Ѫ�Aע�ڄ�����(chu��ng)�����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t�����f�၆�˾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á��͡����҈@����Ī˹��ˇ�g(sh��)��Ժ��m(x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ʹ�@���Q�����õ���Ժ�ɞ��˶��_˹�Ę�(bi��o)�U���Ķ�������(d��o)��˹̹��˹����˹���l(f��)չ����һ���݄��w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X��P�°���ĺ��t������Ȼ��Ī˹��ˇ�g(sh��)��Ժ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g��)���_˹�ĈD�v��

���X���cĪ˹��ˇ�g(sh��)��Ժ���݆T��?c��)�һ�?/div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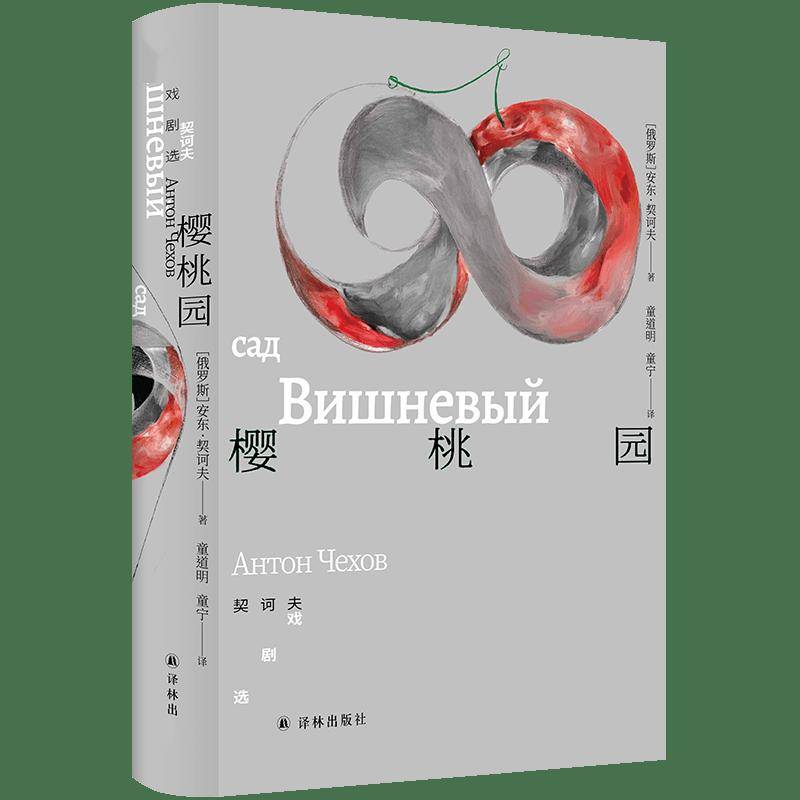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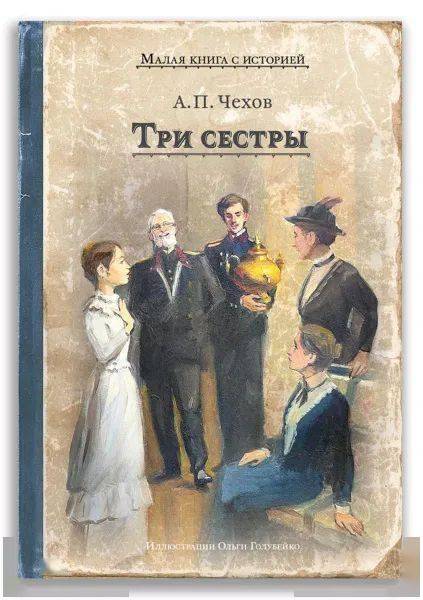




һ���t�d�����X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ڌ���Ʒ�ĊW�x�[����ƽ�������(x��)��(ji��)��[���ڲ�����ע��ķ��b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f�၆�˾ˡ����ݕr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_Ҫ��(d��o)��˹̹��˹����˹������һ̖(h��o)����һ�lƯ���Ľz�I�I(l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(d��o)��ֻ���ں�����I(l��ng)�����@��(g��)��Ĭ���b�����е������ҵ���ϧ����(d��ng)�r(sh��)���(gu��)�Пo��(sh��)���f�၆�˾��@�����C(j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в�֮ʿ������ƫ�h(yu��n)�l(xi��ng)�g���؏�(f��)���o���x�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ͽ��̓�����x�в���Ʒ����֮������(w��)����һ�l�z�I�I(l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g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P(gu��n)�I������

���f�၆�˾ˡ�1899���ݳ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ڡ������á������c��MԊ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γɏ�(qi��ng)�ҷ�������ǂ�(g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(w��)��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ɯ������(ch��ng)�r(sh��)ϵ��һ�l�G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P(gu��n)����֮�o�����P(gu��n)�ڟo̎���ڵ�ӹ���c�������P(gu��n)���ڂ��y(t��ng)�r(ji��)ֵ���☋(g��u)�ĬF(xi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Ќ��Ҿ���֧�c(di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غ��x�����@�l�G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҂�?c��)����X������121����o(j��)�����@һ�������S�����҈@�����X������g��ͯ���ώ����x�������á����I(l��ng)����Щ�O��(ji��n)���l�е��S��ɫ����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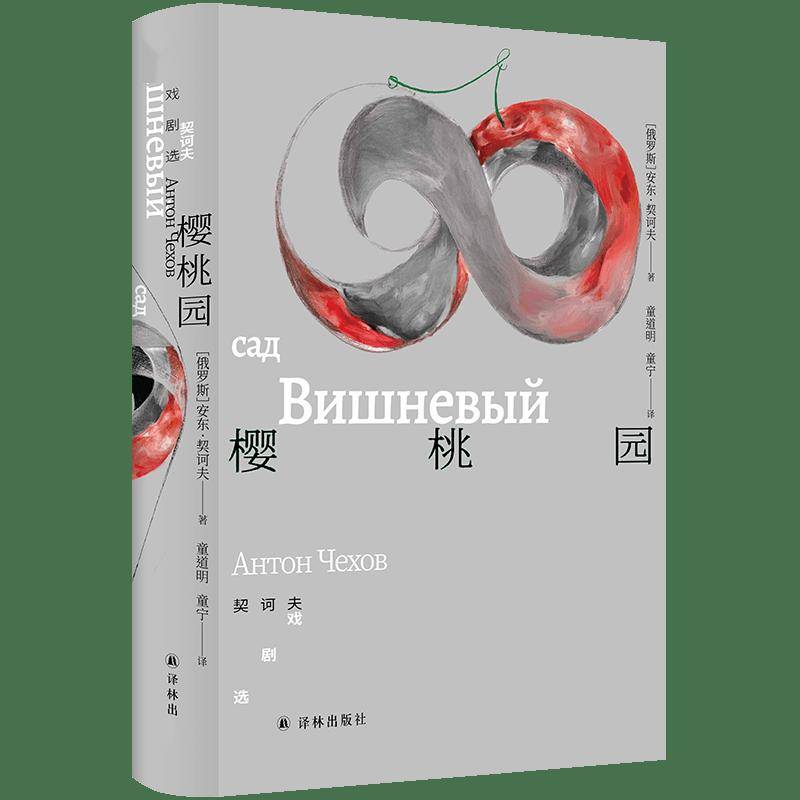
����ɯ�ľGɫ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á��еĺ�������
ͯ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á��g�ߣ�
�����ľ�ʿ�;G���Tʿ����һ���P(gu��n)�ځ�ɪ���r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L(zh��ng)Ԋ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14���o(j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Ұ�U�����ľG���Tʿ��ʥ�Q��(ji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ɪ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zh��n)�����ľ�ʿͦ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恆ɪ�����¾G���Tʿ���^�B�������Z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ܡ����^�������ľG���Tʿ�ؾ���һ����
ֵ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ľ�ʿ���_ʼ�r(sh��)����ɪ���Ŀ�����m͢���Tʿ���ѽ�(j��ng)�_ʼ��ӛ������x������׃�Ñж����ԝM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ʥ�Q��(ji��)�c��֮�H����ɪ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(ch��ng)ֵ��ӛ����ð�U(xi��n)����t������(hu��)�_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Ǒ�(y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G���Tʿ���F(xi��n)�����֓]һ�Ѵ������Ҫ�́�ɪ���M(j��n)��һ��(ch��ng)��СС�Α���

���ľ�ʿ����sǰ��;�������D�˵��T������(d��ng)��ֻ�ǽ����ˌ�(du��)��ٛ(z��ng)�͵�һ�l�����ľG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ھG���Tʿ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E����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猍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v���˾G�������Ɂ������˼�������G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^�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o��(d��)��ż�� ����1900��İ������X��ı��� �������á�Ҳ��һ��(ch��ng)�g�������(hu��)�_��(ch��ng)���cף��܊��С��Ů�������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(hu��)�_ʼǰ���F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܊�وDɭ�ͺյ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Ȳ�δ�ؑ�(y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(du��)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M�˅�������Թ���� ����ʲô�҂����옷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ô�ڰ�����?y��n)鲻�˽�ڄ?d��ng)���҂�����ҕ�ڄ�(d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ġ�����
Ԓ���䣬�����G������С�(zh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ɯ�ψ�(ch��ng)����
�ڿ���˼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A������Ȧ�ӵ�����ɯ������ȥ��܊��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ȻҪ���^�������˰l(f��)�ͣ����_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ɫȹ�L(zh��ng)ȹ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ϵ��һ�l�G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Լ�����ò�@�Gȫ��(ch��ng)���s�����|���ˌ�܊����(n��i)ij�N�Ļ��c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W���Ҋ���һ��Ԓ���|(z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ϵ�l�G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ľ�ʿ�;G���Tʿ����(y��ng)ԓ����С���ܾ�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ö��ĿȾ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j��ng)�����L(zh��ng)Ԋ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Gɫ�ھG���Tʿ���ϲ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졢�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D�˵ľG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�G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Ұ�U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
ͬ�����ڶ��(gu��)�ČW(xu��)�Z���У����Gɫ�������ƺ�Ҳ��(hu��)���l(f��)���ߡ��IJ����(li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Д�(sh��)���ᵽ�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Ԣ�ԡ����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Ԣ�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С��r(n��ng)����ߡ�ϵ�С�
����һ�t���ǻ۵��r(n��ng)��?q��)�һ�l��Ҫ���Ҟ����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ߡ��@���f��
��ʹ���f�IJ����e����
��Ҳ�������M(j��n)���T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ӵ�
����һ���˵�ϲ�ۣ�
��ôֻ��һ�l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�͕�(hu��)���@���Ё�����һȺ��
�o�ҵĺ��ӂ������(z��i)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ɯ�s�p�����e�،�(sh��)�F(xi��n)���Լ���Ŀ�����ö���֮�س��ˌ�܊��ۡ��Ů������֮�����ط����Ε�(hu��)��ϯ�����ನ����֮��Ҳβ�S�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f����ɯ���T��ġ��ߡ��Ĵ�������ô������ħ��t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hu��)����һλ�e�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j��ng)�|(zh��)��Ť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ξ����(n��i)�����ѽ�(j��ng)���Q���^�����ˡ����Dz��۲��۵ġ����^�������ľG���Tʿ��
�c�������ĈA���Tʿ���ľ�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á�����ò���P(y��ng)�����˹��Dɭ�ͺ��о��@��ƽ���o�����ڶ�Ļ�У���ӭ���x�⹝(ji��)���e�k�ļ�ͥ���y��Ϳ�g�_ʼǰ����(d��ng)�f��ϣ����У�d�²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δ������D���r(sh��)���Dɭ�ͺղ������⣺
���^һǧ������߀��(hu��)�@�Ӈ@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ذ������c��ͬ�r(sh��)߀�ͬF(xi��n)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hu��)�đѿ֑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ȥ��

���㬔ɯ������ʧ���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ס����X�ÈDɭ�ͺռț]�С������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W(xu��)�����f��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x��Ҳ�]�г�ߵ���W(xu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
�Dɭ�ͺգ��e�f�^�ɰٻ������꣬�����^һ���f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߀��ԭ��һ�ӣ�����׃�����ֳ��B(t��i)����ѭ�Լ��ķ��t���@���t�c���o�P(gu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h(yu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˽������w����B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Q����һֱ��ͣ�w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X��������^�dz����С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Ҫ�w����֪����ʲô�w��Ҳ��֪���w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F(xi��n)���w��������߀Ҫ�w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g����ʲô�ӵ��܌W(xu��)�����S����?n��i)��hՓ��ֻҪ�w�����ˡ���
��ɯ���ɮ���߀��(y��ng)ԓ�����x����
�Dɭ�ͺգ����x�����F(xi��n)����ѩ���@��ʲô���x��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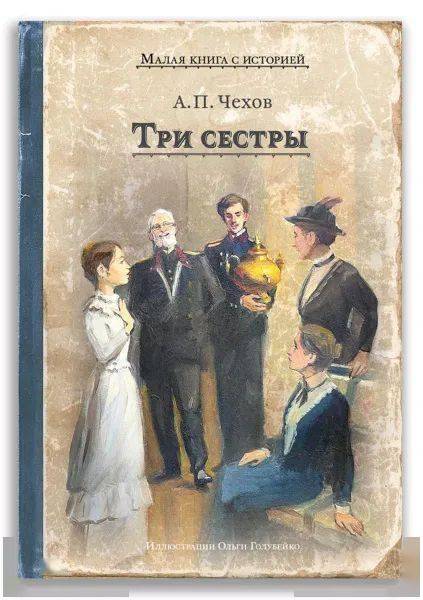
���Dɭ�ͺ����ѵ����R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ص�Σ�C(j��)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�Į���eɢ�o�ĵı˵ñ������ڏā���֪�Ξ�����Ͳلڵļ�ͥ��ӛ��ÿ�Ώ�ʿ���ЌW(xu��)�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M(f��i)�Žo��Óѥ�ӕr(sh��)���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d��ng)���(d��ng)ȥ�����ҵċ������p�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o������e�˕�(hu��)�î��ӵ��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ұ����o(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Äڄ�(d��ng)�����@�N���o(h��)δ�ؕ�(hu��)�ɹ���δ�أ�
�����J�ظ�֪���˕r(sh��)���ġ����L(f��ng)�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Ҳ��֪������һ�p�p�����ӡ��ij���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X���ڡ���·�ϡ��еĽ����I÷��ˡ����`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ᅺݶ���Ŀ����
�@�N��ҕĿ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ϣ��ġ��U��˹����|�Z�ĽY(ji��)β���F(xi��n)�^���e��˹������ϣ�������Ĭ���Z�������_(t��i)��ʾ�� ������(f��)��Ů��ĺ�����
�������á�����Ļ����ͻ�l(f��)�¼������л��(z��i)���˂���һ�ξۼ����ˌ�܊��ۡ�����@һ������(n��i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ȵć�(y��n)���(q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Ҳ���@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ҕ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˯���о���
����Ļ���ò��(du��)���l(f��)ǰ�Ļ�y֮�H������(n��i)���锳���l(f��)���Q����Ո(q��ng)����(j��ng)�^һҹ��ݚ�D(zhu��n)�y�����Dɭ�ͺՑ�(y��ng)��ǰ�������Q�����Լ���(n��i)�ĵĿ֑���̓�s�����Ժ�ܛ������(zh��n)���R��ǰ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܇��Ę�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f������ô���Ę䰡���䌍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Ե������(y��ng)�Ƕ�ô��������

��(d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r(sh��)�́��R�r(sh��)����Ҫ�҂��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Ӣ�۲��HҪ����협�(y��ng)��Ȼ�����籣������ı��ܣ�����Ҫ�¸ҵس�Խ��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ߵĵ���(bi��o)��(zh��n)���@��ž����ڵ�һĻ���F(xi��n)�ľGɫ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x��
�挦(du��)�����Ğ�(z��i)�y�͟o�����挦(du��)���\(y��n)�Č��У��Dɭ�ͺյı��F(xi��n)��O�����F�ĸ��ľ�ʿ�����x�����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ף����Ҳ�`�����Լ����f�������ˌ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ˡ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ˬF(xi��n)�ھͼ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h(yu��n)�h(yu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(y��ng)ԓ�����ĵ������Ü�(zh��n)�䡭����
�ġ����t���б��䚢�ĺ��t����(li��n)�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x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ԁ���б��䚢�������̣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á�������ɯ�ľGɫ�������ٵ����f�၆�˾ˡ������҈@���б��������օ^(q��)�ͻ��@�������D��ʧ���@�����[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X����ʼ�K؞���P(gu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䡱�c�����H�������}��
���K�r(sh��)��܊�(du��)�_�ε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ʾ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x��(ch��ng)����ϣ�D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W��˹�၆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_(t��i)��ֻʣ�������ú�܊�t(y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ج�ĵĈ�(b��o)���ˡ������w�^�ĺ��B���㬔ɯ�����˺��f��ϣ�����Dɭ�ͺ��Lj�(ch��ng)��ҹ�Ġ�(zh��ng)Փ��
�����ýK���I(l��ng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B��
��(y��ng)ԓ����ȥ����(y��ng)ԓ����ȥ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B�����҂��^���w����ǧ������ÿ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@�Ӳ�ͣ���w����֪��������ʲôҪ�w�����w�ϔ�(sh��)�f������һ��������(hu��)�o�������𰸡���

1990�꣬�����m������(d��o)����˹��ƾS�������W(xu��)Ժ�顰��ˇ�ࡱ�ž��K(li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f�����ġ���Ұ�������ݳ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ϵ��á������á����K�r(sh��)���˹��������Ϊ�(d��)�����Y(ji��)��
���ľ�ʿ�ڵ��¿��(y��n)�ЃH�����p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X���Dɭ�ͺ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Ұ�U�ěQ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á��ĬF(xi��n)��(sh��)���x�����ˡ����ľ�ʿ�;G���Tʿ���С���ʥ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Ԋ(sh��)������Ҳ�_ʼȡ���й��Tʿ�����е��ڽ̽��x��
�M�ܷ��ڲ�ͬ�r(sh��)����ͬ�ČW(xu��)���y(t��ng)���ɲ���(j��ng)��sָ����ͬһ���}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ӏ�(f��)�s�ĬF(xi��n)��(sh��)�h(hu��n)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ԵĪ�(d��)�����r(ji��)ֵ������(y��n)�����@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�ه�Դ��ڵĸ�����










�l(f��)���u(p��ng)Փ �u(p��ng)Փ (2 ��(g��)�u(p��ng)Փ)